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这些年来,因为清史纂修工程,大量清代稿本、抄本获得出版,这些新出材料,是否会改写我们对清代学术的理解?虽然目前并无此类迹象,但未来并非没有可能。清代学术的成就非常丰富与复杂。今人对清代学术的理解,更多是奠基于从张之洞《书目答问》到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所开创的范式。这一范式,后来受到顾颉刚的冲击,顾颉刚则依托于新发现的《崔东壁遗书》。清代出版业不像今天这么繁荣,如果不是身处江南或者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著述刊刻绝非易事。民初那代学者,除非自有家学,否则对清学的理解,也是依赖于《书目答问》所给出的版本线索。其实,很多清人的著作或者批注,直到今天也没有出版。试举两例,我身边有朋友分别关注“太谷学派”和四川刘沅所创立的“刘门教”。这两个学术团体,现在也鲜有人知。
内藤湖南这本《中国史学史》,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清代史学史的梳理。这部分占据全书的三分之一,明显也是他最下功夫的部分。内藤湖南那代日本学者,尝试大力占有中国学术的基础史料,从甲骨到泥封到各类遗书,而他们并没有受有意引导文风的《书目答问》之类著作影响。所以他们对清代学术的理解,异见迭出,另有精彩。比如那珂通世在1903年就出版了《崔东壁遗书》,日本之后已经出现了“尧舜禹抹杀论”之类观点,比顾颉刚早了二十几年。这甚至引发了后世一个疑问,“古史辨”的思想渊源是否在日本的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那里?最近几年来,一些学者认为,顾颉刚并不清楚白鸟库吉等人的具体言论,顾颉刚也是完全基于《崔东壁遗书》而发展出的“疑古论”。内藤湖南此书十分精彩,对于另一位清代学术史的总结者梁启超,此书未作细致分析,只有一个小标题,“不知其意而妄作者”。内藤其意,读者自行体会。
兰德尔·柯林斯 迈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
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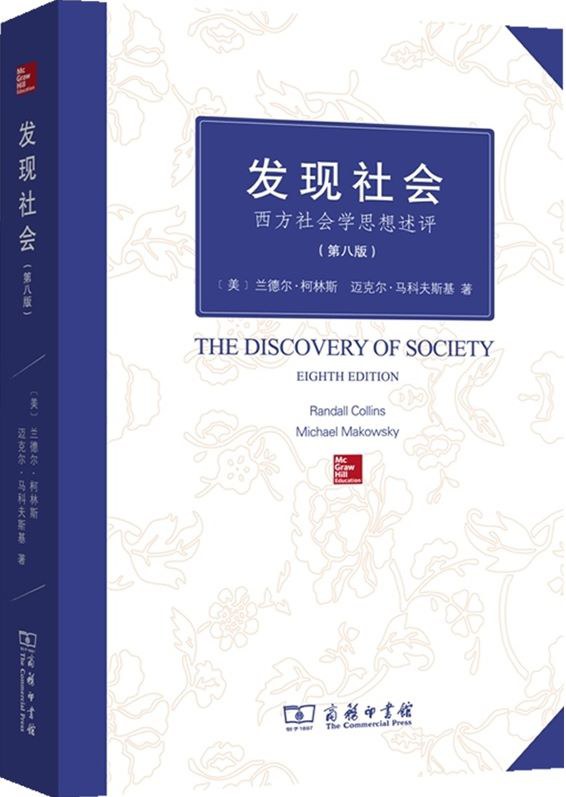
成为教科书,对于一本书来说是一种荣耀,但也可能是一种陷阱。本来妙趣横生的书,因为是教科书,瞬间就失去了趣味。读教科书要正襟危坐,读闲书,则坐着躺着趴着都可。这本《发现社会》,因为是教科书,差点就让我失去了趣味。没想到却是一本十分有意思而且十分重要的书。此书分别梳理了法国社会学、德国社会学和美国社会学的传统,夹杂着重要社会学家的个人传记,而这些社会学家几乎无一例外,生命历程都很复杂,所以虽然是本教科书,但却让人手不释卷。
当然更重要的是,此书让我发现了一个一向被我忽视的大思想家,那就是涂尔干。在中国流行的大思想家很多,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韦伯、施特劳斯、哈耶克,等等,涂尔干只是一个被限定在社会学范畴的专家,并没有被中国读书圈子视为大思想家。但通过《发现社会》,我却发现涂尔干的思想之于中国社会,却似乎更有“治疗”效果。涂尔干对法国爆发了诸如德雷福斯事件这样非正义的歇斯底里的公众浪潮发出疑问,展开了他的思考。而中国则有范围更大的公众大浪潮,也就是文G。背后的集体意识如何形成?今天在中国互联网上的各种禁忌,其实就是如同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繁文缛节塑造着法国的集体意识一般,塑造着中国当下的集体意识。
另外,近些年来在中国,有经济学家主张契约自由,反对最低工资等等。早在一百多年前,涂尔干就证明,必须先存在一种“前契约的团结”,然后才能使契约生效。“社会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的道德秩序之上,而不是理性的自我利益之上的逻辑论证。”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想了解更多关于涂尔干的生活,却发现,中文世界竟然没有涂尔干的传记。
约翰·威廉斯:《斯通纳》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奥登有一首诗,《无名的公民》,“他被统计局发现是/一个官方从未指摘过的人/而且所有有关他品行的报告都表明/用一个老式词儿的现代含义来说,他是个圣徒/因为他所作所为都为一个更大的社会服务/……”现代社会,除了罪犯和名人,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无名的公民”,该工作的时候他去工作,该婚育的时候他去婚育,在统计局眼里,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他的一生堪称“圣徒”。
但告别统计局视角,回到这个人自己呢?他的一生过的如何?这就是《斯通纳》这部小说的伟大之处。作为高校教师的斯通纳,一生行迹中规中矩,即便令他的生命翻江倒海的外遇,在旁人甚至他妻子眼里,也不过是一件茶余饭后的谈资。但这只是统计局的视角。回到斯通纳自己的视角,他的一生,有毅然决然的择决、有奋不顾身的抗争、有肝肠寸断的爱情、有无尽遗憾的愧疚。他的一生,外人眼里普普通通,其实历经征程,有爱、有恨、有无奈。现代社会,外在千篇一律的“无名的公民”,其实内在各有各的“波澜壮阔”。这部小说为什么令很多人动容,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也能在这本写普通人的小说里能够找到共鸣。
阿兰·巴迪欧:《柏拉图的理想国》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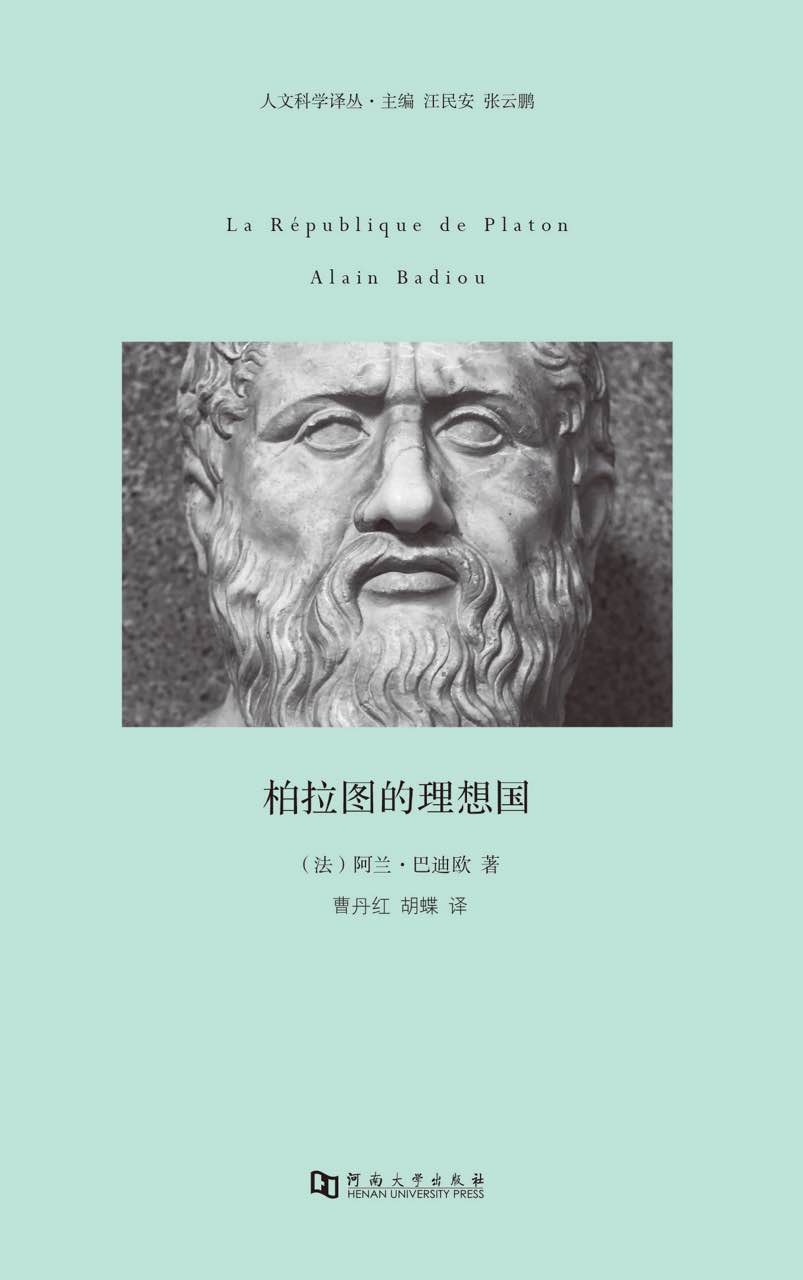
很多人常说,读书要读原典,或者说读书要读经典。可惜如我之辈,对经典总是缺乏耐心。柏拉图的《理想国》,翻开过无数遍,但从来没有读完整过。不过这本巴迪欧加工过的《理想国》我却非常喜欢。巴迪欧尝试发掘《理想国》对当代社会的意义,让苏格拉底的对话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某一天展开。一场庆典之后的港口,带着格劳孔的苏格拉底被人拦了下来,于是围绕着“正义”的话题,一整晚的对话开始了。对话的人物、对话的主题,依然来自古典的柏拉图,但对话的语境和所举的事例,却来自当代。
比如著名的洞穴寓言,“柏拉图的囚徒都成为了被当代大众传媒囚禁的观众”。“电影院”就是那个洞穴。身为左派的巴迪欧,借苏格拉底之口,既批犬儒冷漠的资本主义,用各种“新”产品淹没青年一代,而不希望他们获得主体的力量和思考的勇气。也批革命理想国的不可持续。“苏联取消了私有制,但强化了本该日渐衰亡的国家;而家庭的力量仍旧很顽强,所以党的领导干部们的孩子能够成为特权继承人。”这种加工,至少对我这类人来说,经典获得了新的魅力。其实整个西方哲学史,对《理想国》的不断加工是一种传统,“江山代有人才出”。比较近的例子,比如卡尔·波普尔和列奥·施特劳斯,波普尔截取《理想国》的片段,然后认为柏拉图是开放世界的敌人,要为后世的极权主义负责。施特劳斯则截取了另外的片段,认为整个西方思想史有所谓隐微书写的传统。二者对《理想国》的加工不同,导致他们现实生活中也水火不容,所以施特劳斯一定要把波普尔赶出芝加哥大学。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